◎毛翊宇(勞動視野工作室)

就在不久前的6月9日晚上七點,繁榮寧靜的台北市仁愛路,數百名警察突然來勢洶洶,在永豐餘集團總裁何壽川住處集結,拉起蛇籠,不讓民眾通過,準備大動干戈。然而,究竟這數百名警察所為何來,他們包圍的對象是誰?在永豐餘集團總裁何壽川家門前,有張小小的桌子,鋪著全白的桌巾,上面擺著兩根蠟燭及一盞香爐,插著、擺著幾根祭祀用的香,香爐的後面,立著一幅莊嚴肅穆的遺像,韓國工人裴宰炯頭戴紅色布條、身穿紅色背心、眼神柔和而堅定,這就是他為Hydis工人挺身抗爭時的模樣,而他在這場抗爭中,在無奈和悲憤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一旁陪伴裴宰炯的,是他遠從韓國渡海來台的妻子李美羅,以及和李美羅一同前來的工會幹部們,在警察強制驅離和清場以後,他們都遭到了逮捕,現場祭拜用的香散落一地,又一場工人在黑暗中掙扎的悲歌悄悄落幕。
其實,這已經是韓國工會的朋友今年第三次來台了,他們要抗議的對象是台灣的大財團永豐餘和其總裁何壽川,這場艱難的跨海抗爭,所對抗的是什麼,本文以下將提出觀察。
只要專利不要工人的元太科技
這一切的引爆點,是今年1月時,Hydis公司的最大股東台資元太科技(E ink),在董事會上決議關閉Hydis在韓國利川的生產線,並且計畫日後要陸續關閉全韓國的生產線,讓Hydis成為一家沒有生產線,只靠專利技術授權獲利的公司。元太科技關閉生產線這一措施,根據韓國金屬工會的統計,將造成多達800名工人失業,其中400名為Hydis公司的既有員工,另外400名為在Hydis外包廠商工作的員工,此決定對工人的衝擊之大可見一斑,然而元太科技在做成此決定前,完全沒有和工會進行協商。為什麼元太科技會做出關閉所有生產線的決定呢?是因為沒有訂單?還是因為生產線的經營產生虧損?兩者皆否,當元太科技決定關閉生產線時,Hydis公司仍有訂單,因此停產的決定讓Hydis的外包廠商蒙受巨大損失,但是元太科技寧願挨告也要關閉生產線,而根據工會表示,Hydis的年度盈餘仍達新台幣29億元,那麼,究竟元太科技在打什麼算盤呢?
讓我們先從Hydis公司這十幾年的歷史談起,Hydis公司,原屬韓國現代集團,是一間擁有TFT-LCD液晶顯示器、EPD電子紙技術,以及廣視角專利技術(Fringe Field Switching, FFS)的半導體公司,Hydis公司在全盛時期,曾一度擁有多達近2,000名的員工,年度營業額更高達新台幣288億元。但好景不常,2003年,自中國面板廠京東方(BOE)買下Hydis公司之後,將部分廣視角專利技術賣給同業,並且在經營Hydis的三年多期間,從不投資更新生產設備,也不投資技術研發,無心永續經營只圖販賣和授權專利技術的收入,這樣的做法,當然讓Hydis公司大受其害,營業額暴跌至僅剩新台幣52億元,隨後中國京東方便宣告破產,Hydis工人首當其衝,當時造成了600多名員工失業。破產後的Hydis公司積極尋找買主,終於在2007年,台灣永豐餘集團投資的元太科技表明有意願接手,有了之前中國京東方的前車之鑑,Hydis工會擔心元太科技會重施「吃了技術就跑」的故技,因此元太科技也做出「會好好經營公司」的承諾。
那麼之後又如何呢?根據韓國金屬工會Hydis支會,在永豐餘集團和元太科技買下Hydis公司這段期間,靠著專利技術總共賺得了新台幣上百億元的權利金,但用在生產設備上的投資卻微不足道,僅佔公司收益的2%,只足夠支應故障零件的修理。這樣的經營方式讓Hydis公司的生產設備逐漸落後競爭對手,最後導致元太科技在專利授權和產品生產的營收比重,不斷向專利授權一方傾斜,因此縱使Hydis公司至今仍持續獲利,卻仍然作出了關閉生產線的決定,這種行徑簡直就是複製了中國京東方的做法,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將員工全部甩開,卻繼續佔有專利技術,對Hydis工人而言,這樣的行徑就像是在寒冬之中,將勞工拋到大街上一樣殘忍。工會在韓國要求元太科技出面和工人協商,但元太科技卻表示,決定權在永豐餘集團手上,於是韓國工人便開始了漫長的跨海抗爭之路。
資本的貪慾對抗工人的生計
這場Hydis工人與台灣永豐餘集團之間的抗爭,從今年2月開始就一直持續至今尚未完結,在台灣工運界朋友的熱心幫助下,成立了「台灣聲援Hydis工人連線」,Hydis工人在台灣歷經了散發傳單、三步一跪遊行、向勞動部、總統府陳情、親至何壽川家和永豐餘股東會表達訴求,要求「撤回關廠」、「何壽川別落跑」、「撤回解僱」、「何壽川出來面對」,希望保住工人的工作權,永豐餘集團好好經營Hydis公司。在抗爭之中,還發生了工會幹部裴宰炯因受到資方對工會以民事賠償相逼,而壓力過大上吊身亡的悲劇,除此之外,Hydis工人和台灣聲援者不只一次遭遇了警察的驅離和逮捕,大部份的韓國工人還遭到即刻遣返,這場抗爭可謂困難重重,舉步維艱,然而,最終的結果還未決定。不論爾後會不會出現轉機,此時此刻為Hydis工人的鬥爭做點思考,理出頭緒,縱使沒有辦法轉化成當下現實的成果,總是有些積極意義的。
韓國Hydis工人在台北街頭散發的傳單上寫著:「我們以為台灣的企業和中國大陸不一樣」,以及「一間真正的國際級企業應當要有社會責任」,但是很遺憾,為什麼不只在韓國,甚至在台灣、中國大陸沿海等地,廠商惡性關廠的事件層出不窮,這是有原因的,當類似事件如此浮濫,我們實在很難再歸咎於少數無良企業的個別行為,承認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工人必須有所警惕和防範,不論經營者平常看起來多麼「有良」。就以元太科技為例,董事、股東會甚至銀行團,這些對公司的資本有決定權的人,如果你試著去瞭解他們的思考方式,你會發現,他們最終在乎的只有:提高利潤,並順帶關心削減成本和市場競爭。握有資本的人,總是想著以最小的不確定性、最低的成本賺取最高的利潤,當有兩種不同的經營策略供他們選擇時,工人的生計重要性遠遠排在利潤之後,企業形象偶爾受損也無所謂,只要這對資本的獲利沒有太大影響。
這就是為什麼元太科技就算持續獲利,也不願意投資更新生產設備,反而想要靠已經開發出來的專利技術賺錢就好,問題不在於是否獲利,而是把資本投在哪個用途上,可以用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報酬,至於失業工人受到的衝擊,很抱歉,這不會列在企業的財務報表上,所以董事顯然不是很重視。但這是站在董事和股東的角度看企業,企業非得這麼運作、非得按照利潤最大化的目標行事嗎?當然不是,對工人來說,企業存在的目的不僅僅是營利和滿足資本的貪慾而已,最重要的是,企業藉由生產能夠滿足社會需要的產品,為工人提供就業機會和收入,這才是企業存在的意義。然而,企業經營者卻不是這樣想,例如元太科技,寧願任由生產設備老化、捨棄訂單不接、讓800多名員工和他們的家庭承受生活頓失所依的痛苦,也要選擇坐收權利金的經營方式,經營者和工人對企業的認知有根深柢固的衝突,就是Hydis工人抗爭的深層原因。
失靈的政府和缺席的工會力量
不論是韓國或者台灣,企業所有者都享有至高無上的「關廠權」,一條能養活上千名工人的生產線,生死存亡全在資本寡頭一念之間,這種極不平等的權力結構,就是我們每日生活其中的經濟現實,政府和法律能否發揮制衡的作用?從這次Hydis工人的抗爭中,我們也可以窺見一些端倪,韓國《勞動基準法》規定,雇主須有「經營上的急迫必要性」或「防止經營持續惡化」方可解僱勞工,然而Hydis工人也批評道,這樣沒有明確判斷基準,模糊不清的用字,使得理應保障勞工的勞基法,反而成了資方得以濫權解雇的漏洞。今年3月,當Hydis工人到台灣勞動部陳情時,勞動部的回答是,由於本案涉及台灣企業跨國投資,本國法律並不適用,只能要求事業單位應遵守當地法令,姑且不論這個法律見解正不正確,勞動部只想把問題踢回韓國。面對企業所有者橫行無阻的「關廠權」,法律只是徒有其表而已,政府制衡資本的功能,已經完全失靈。
面對盤根錯節的社會不公,孤立無援的工人只能靠自己。靠有良知的社會大眾雖可將鬥爭基礎擴大到社會之中,組織外部的壓力,討回一點應有的尊嚴,然而,如果要為勞工運動展望未來,也許工人還是要回到勞動制衡資本的著力點上。在這場抗爭中,我們看到許多熱心的勞工團體和民眾相挺,但是我們沒有看到永豐餘集團旗下的公司有工會出來發聲,沒有看到有工會出來監督資方,提醒基層會員要警惕、要從Hydis工人跟永豐餘的抗爭中吸取教訓。事實上這不只是永豐餘的問題,台灣勞工的工會組織率和工會意識普遍低落,這個弱點總是在每次的抗爭中暴露出來,然而只有一步一腳印的努力,才能扭轉這個頹勢。我們也沒有看到,目前熱衷2016大選的諸政黨中,有哪個願意投入這場抗爭,提出將資方獨攬的「關廠權」還給工人的政策。
不只對韓國而言,對台灣和整個亞洲的工人來說,都是場值得記上一筆的戰鬥。它向我們揭示了今日工人的處境,在大型企業經營日益國際化之下,面對著跨國資本的肆虐濫權,唯利潤是圖,工人如何掙扎著捍衛自己的權益、如何對抗不同國家的資本、和不同國家的工人們並肩作戰。不論今日韓國Hydis工人抗爭的結局如何,這絕對不會是最後一場類似形式的抗爭,而且也絕對不會是一場跟台灣工人的命運無關的抗爭,我們務必記得,在資本全球化的年代,發生在Hydis工人身上的事情,完全有可能發生在每一個台灣工人身上。Hydis工人已經用他們的行動,暴露了問題,而我們該做的,就是牢牢記住他們的經驗,尋思今日該如何積蓄力量,以求未來發動更有效的抵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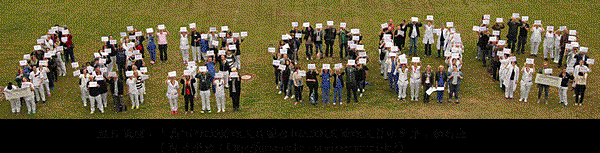

近期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