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張鑫隆 教授(勞動視野工作室顧問、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

勞動只是為了生存而存在嗎?
我常問學生勞動法保護勞工的目的是什麼?通常得到的答案是:「因為勞工是弱勢」;如果有一點權利概念的學生會回答:「為了保障他們的生存權。」
沒錯,生存是勞動最根本的目的,任誰也無法否定。但是占據人一生大半時間的勞動,只是為了生存嗎?
最近上映的日本電影《戀戀銅鑼燒》是在介紹一位長期被隔離的漢生病復元者,以及一位受刑人回歸社會的故事,勞動不是電影想要傳達的議題,但是劇中關於賣銅鑼燒的店長和在店裡做紅豆餡的阿嬤讓我聯想到「勞動」這個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過程,到底有什麼意義?特別是對勞動法的存在而言。
漢生病這種感染性極低的古老疾病並不會致命,只會留下肢體或顏面殘缺的後遺症,然而日本政府在1930年代基於優生主義的思想,開始對漢生病患者進行強制隔離,並且在收容所中實施強制勞動、強制墮胎、強制結紮等不人道手段。同時,官方為強化收容的效果,將漢生病宣傳為非常可怕的疾病,造成社會對患者更深一層的歧視。
戰後漢生病的特效藥已經問市,更沒有隔離的必要,但是日本政府認為患者受到社會排斥,為繼續為維持收容所的預算、提供患者的照顧而未廢除隔離法,一直到1996年才廢除。這部電影所要訴求的就是國家對患者的人權侵害而造成的社會偏見,試圖透過一位患者阿嬤回歸社會的勇氣和其生命的美好,來讓世人理解漢生病康復者想回歸社會的意志,並非獲得同情,而是獲得和一般人同樣的對待。包括其他社會邊緣人或弱勢者也是如此,因為他們認為他們生命並沒有被環境所打敗。
他們被剝奪一生所有發展的可能性
故事是這樣展開。一個受刑人出獄後找不到工作,不得不由房東兼老闆以「偽裝承攬」的模式,借錢給他開一間小小的銅鑼燒店當店長,一邊賺錢維生,一邊還債,完全沒有休假。另一方面,因為1996年日本政府廢除漢生病隔離法而得以回到社會的漢生病康復者的75歲阿嬤,嘗試以她在收容所中做紅豆餡50年的手藝來應徵這家銅鑼燒店的員工。這位店長在意阿嬤年紀太大不堪負荷工作而拒絕,儘管阿嬤不斷強調再低的工資都願意做,也得不到店長的青睞。一直到店長試吃了阿嬤做的紅豆餡後,告知阿嬤要僱用她的一剎那,阿嬤高興到說不出話的表情,也許一般人的感受不會很深刻,但是看在曾經協助過漢生病患的人或了解台、日漢生病患歷史背景的人眼裡,那是令人無限感動的一刻。
這樣的情節不禁令人聯想到在台灣有相同背景的樂生院已故的院民湯祥明,他是一個詩人也是一個畫家,在解除隔離後試圖想回歸社會尋找工作,好不容易被錄取了,但是當他拿出身分證被看到是樂生院的地址後,工作的希望也就隨之破滅了。
國家長期的隔離政策造成了社會對這種疾病錯誤的認識,導致患者受到嚴重的歧視無法回歸社會,日本律師團因而向法院提出了國家賠償訴訟。但是日本政府辯稱,由於患者回歸社會的意願不高,而為獲取預算維持療養院來提供患者生活和醫療的機能,所以才一直沒有廢除隔離法。
2004年日本熊本地方法院判決日本政府應負國家賠償責任,其理由認為漢生病患者受到長期隔離,有人被迫中斷學業、有人喪失工作機會或被剝奪就業機會、有人失去結婚成家和生育兒女的機會、有人失去親人共同生活享受親情的機會,他們共同的的特色是「被剝奪了做一個人本來就應擁有之一生所有發展的可能性」,也就是日本憲法第13條所保障之「幸福追求權」的侵害。日本憲法之幸福追求權並非政策性的規定,而是以人的尊嚴應受到最高尊重為前提,對於自己人格形成的過程和方式有自我決定的權利,就如同「自己是自己一生的作者」之比喻一樣,在這種基本的價値思想下,自己一生的過程如何選擇是一個不可取代、必要且不可欠缺的權利和自由 1。
以自己之偏見來「替別人決定幸福」的價值觀
電影所要傳達的不只是如同一般影評所講的那樣,僅僅是一般社會的偏見或歧視的問題而已,而是要讓大家去思考造成社會對漢生病的偏見的背後真正的元凶:國家剝奪其「一生所有發展的可能性」的思維。
當初建議日本政府對漢生病患者進行強制收容的光田健輔醫生,除了受到當時盛行的「民族淨化論」和優生主義的影響外,另一個關鍵的理由是,將流落街頭無家可歸的患者強制收容到療養所中,給予免費的照顧是對患者最有利的選擇。這種溫情主義的思維和後來日本政府辯稱為維持福利預算的分配來繼續照顧患者所以才未廢除隔離法的理由一樣,都是以自己之偏見來「替別人決定幸福」的價值觀。
熊本地院判決重新開啟了漢生病患「一生所有發展的可能性」的大門,片中阿嬤勇敢地將他在收容所中做了50年紅豆餡的巧藝向店長毛遂自薦獲得認同,儘管社會的偏見仍深,她還是很滿足的走完最後的人生。
勞動法是為勞動保護而存在?還是為解放勞工不自由而存在?
勞動法的世界裡,勞動常被理解為不自由、受支配的代名詞,所以勞動從屬性可以說是勞動法用來判斷適用對象和保護程度的重要根據。但是勞動保護法令的建構是因為勞工處於不自由的弱勢地位、生存權受到威脅而存在?還是為解放勞工這種不自由的狀態而存在?兩者不同的思維,影響勞動法的發展方向非常大。
在個別法的關係上,日本的「終身僱用制」眾所皆知,也因此在判決上形成非常嚴格之解僱權濫用禁止法理,後來被規定在勞動契約法中,形成了日本獨特的內部勞動市場的勞資關係。但是這樣的企業制度並非以互信關係作為基礎,而是由過勞、單身赴任、職場霸凌、性騷擾等代名詞所組合成的「支配共同體」來運作。
生存權的主張固然可以獲得國家某程度的保障,但是也因為是交由國家政策決定的一種權利,只要具有某種程度的保障或補償,勞工眾多的權利被國家假公共利益之名所犧牲亦無話可說。例如雇主可以片面改變工作規則,只要經過主管機關核備和揭示就可發生改變勞動契約的效力(日本還要加上聽取工會的意見),甚至最高法院還認為工作規則即使未經核備,也具有私法上的效力。在集體法方面,罷工被日本最高法院解釋為是為維持生存的手段,公務員的罷工權因此被身分的保障所取代;我國公務員連罷工權都未被承認,教師的罷工權更臣服在受教權之下,被絕對的禁止。勞工要對國家或雇主表達抗議的罷工,也因為與勞動條件之團體協商無關而被認為違法。
勞動的方式和內容的選擇 也是勞工一生所有發展的可能性之一
進入90年代後,國家為配合企業競爭,以建構所謂「社會安全網」為配套,提出大量的勞動彈性化政策。其目的是要讓企業擺脫正職勞工的人事負擔,使大量勞工流向外部勞動市場,擴大非典型勞工的僱用。所謂的社會安全網無非就是透過非典型就業的促進來隱藏潛在性的失業率,亦或透過失業給付、職業訓練或對企業的補助來緩和失業率所造成之政權的壓力,特別是在選舉之前。
這種以勞動保護為名的勞動彈性化政策,是以滿足企業降低成本的需求為目的,並非為勞工的多樣化所為,所以非典型就業多是出於不得已的選擇。上個月(2015年9月)日本國會通過修正的勞動者派遣法,打破了派遣之臨時性和專門性的原則性限制,以長期僱用的保障作為前提,解除了期間和對象的限制,使派遣勞動可能成為勞工終身的工作型態(參見〈日本勞動者派遣法沈淪記〉一文)。無疑的,這種「長期僱用」的保護是用「非典勞動的隔離」所換來的,換句話說,日本「終身僱用」的神話破滅,將由「終身派遣」所取代。
我國勞動派遣立法受到工會強力反對,一直沒有進展,今年勞動部改以《派遣勞工保護法》的型態出發,迫使反對立法的勞工團體要回到勞動法的原點來思考:勞動法應該是為勞動條件的保護而存在?還是為解放勞工不自由的狀態而存在?兩者也許有併存的可能,但也必然有偏廢的問題。
從日本漢生病隔離政策所獲得的教訓來看,我們要提醒勞工團體和立法政策的決策者,即使有再好的勞動保護,如果因此而使非典型勞動型態成為勞工無法改變的選擇,可能將重蹈「替別人決定幸福」的覆轍,因為勞動的方式和內容的選擇自由也是勞工一生所有發展的可能性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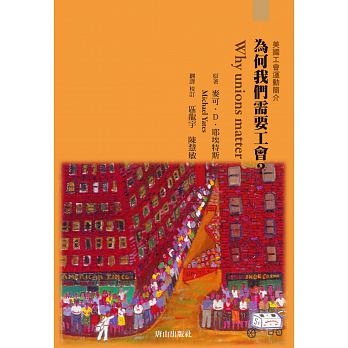
近期留言